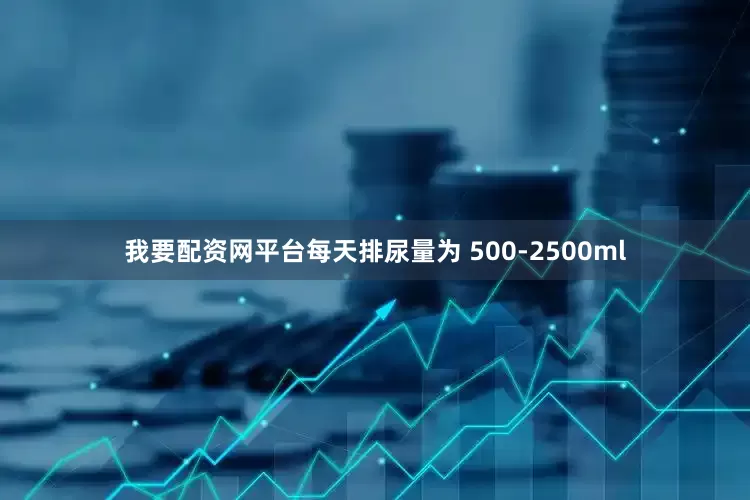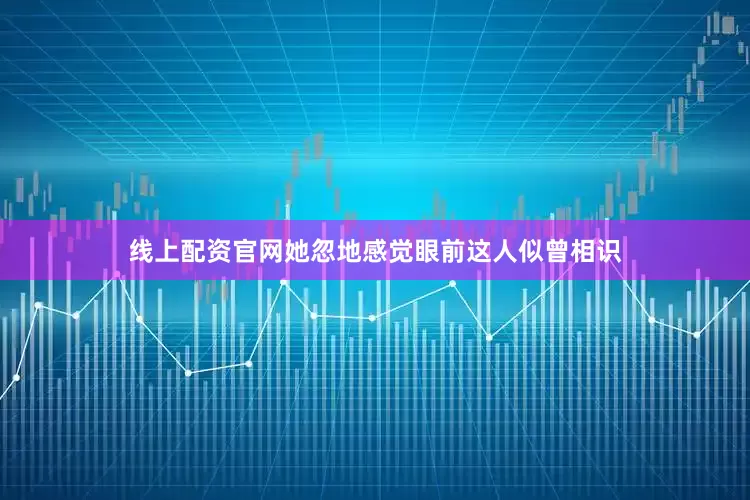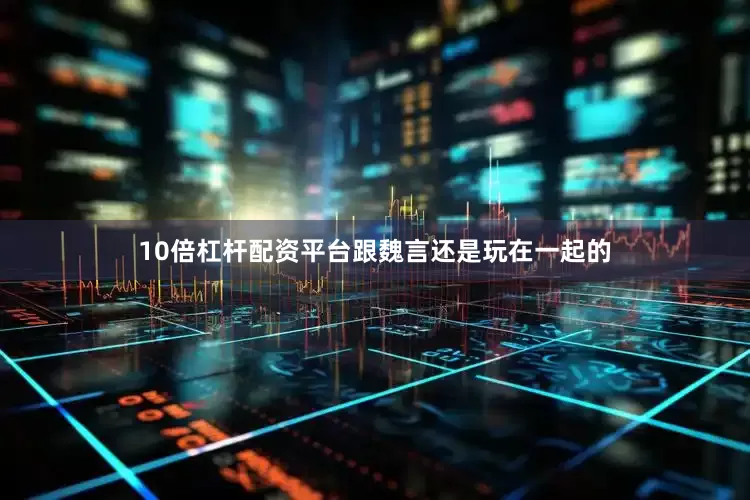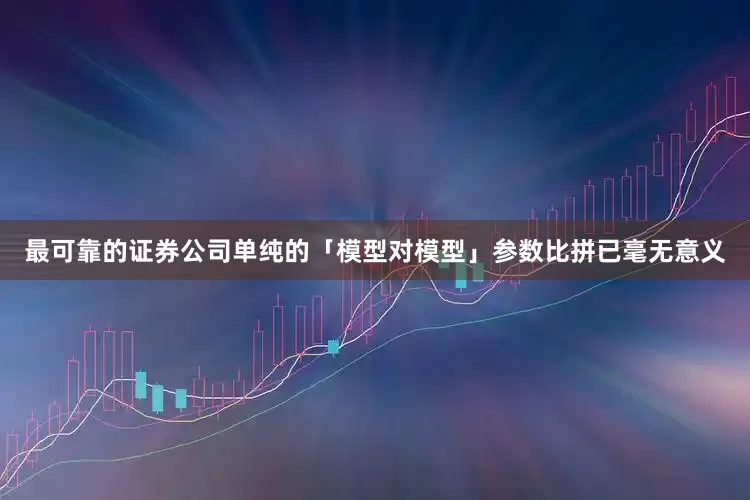民国二十五年,也就是公元1936年,7月,《益世报》曾连续报道了有关“荷花之死”的详细情况。读来令人唏嘘不已,心头沉重。
荷花本姓张,至于她的名字,始终无从得知。她进入“班子”后,便没有再用过自己的姓氏,原因自然是出于对顾客面子的考虑。因为她与“同门”间有些不便言说的尴尬,问及姓氏时,总觉得不合适。所以,窑子里的姑娘们,名字是有的,却无姓氏。即使她们有个名字,也多是一些柔和的、符合娱乐圈风格的绰号,听着顺耳,叫起来顺口。荷花便是其中一位,至于她真实的名字,没人知道。
荷花来自杨柳青,那时她不过刚满十八岁。她被卖到侯家后,成了云裳班的一员。初来乍到,她正值青春年华,容貌艳丽,姿态出众。更为难得的是,她出生于书香门第,受过良好教育。她有着一双巧手,文艺素养高超,不仅能挥毫泼墨写一手好字,而且能画出一幅幅精美的荷花。正因如此,班主金大宝便以“荷花”作为她的艺名。
展开剩余75%荷花的才艺为她带来了不小的收入。她画的荷花,甚至以千元的高价出售。某位居住在津门的大文豪曾用高价购得她的一幅“枯荷听雨”。然而,再多的才华也改变不了她命运的轨迹,她终究还是沦为一位命运多舛的花魁,沦陷在万千客人怀中。
荷花刚进云裳班时,金大宝对她极为宠爱,视她为摇钱树,百般呵护。因为荷花的名气,连租界里的洋人也时常慕名前来。为了取悦这些洋人,班主时常安排车辆接送荷花,甚至为她提供高档的住宿和奢华的待遇。而荷花的每次出场,都会带来可观的收入。金大发自然从中捞取一部分“大头”,而荷花自己则可拥有剩下的部分。于是,荷花的财富也积累了起来。甚至有人说,她积攒的钱足以自己开班子,但她却并不具备经商的头脑,只是单纯地过着“花姐”的日子。她知道自己的身世,清楚这个行业的性质,于是努力积攒着钱,而不去随便挥霍。
然而,风头太劲的人往往会陷入孤独和疲惫之中,荷花便是如此。她的私生活几乎无所遁形,几乎没有私人时间休息。有时实在累得无法忍受,她便会独自关上房门,默默流泪。金大发虽然心知肚明,但依然不断劝说她接客,然而荷花却坚定不肯。
无计可施的金大发最终想出了一个“妙计”,托人从日租界的东洋商人那里弄来几支吗啡。金大发告诉荷花,这是一种由洋人使用的神奇药物,可以瞬间消除一切疲劳、痛苦。荷花天真地相信了金大发的话,尝试了后,果然感到全身轻松,痛苦和疲劳瞬间消失。她开始迷上了这种感觉,逐渐对吗啡产生了依赖。
然而,金大发对荷花的依赖感到可惜,他并不愿意为荷花买药,而荷花已经上了瘾,不得不自己掏钱,求金大发帮她购买。而金大发借机剥夺了她的积蓄,让荷花愚昧无知地为她的毒瘾埋单。
荷花虽然不是聪明人,但她知道自己的未来并不长久。她意识到自己年轻的美貌和才艺迟早会被时间磨灭,而她所从事的行业注定无法维持长久。于是,她决定趁年轻寻找到一个可以从良的好男人。这位“好人”终于出现了,他是一位家住金家窑的油号少东家,年轻英俊,财貌双全,是个值得托付终生的好人。
荷花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情愫,而小实也情深意切,两人一见钟情,迅速定下了婚约。然而,荷花的秘密始终未曾透露,她未曾告诉小实自己已深陷毒品的泥沼,担心这一秘密会让小实对她心生嫌弃。虽然小实并不知道,但荷花的生活依然未能好转,慢慢地她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几乎都花光了。
小实从未察觉到荷花的困境,直到有一天,荷花偷走了他的一块名贵的西洋怀表,并将其典当。小实得知怀表失踪后,四处寻找,最终发现是荷花拿走了这块怀表。经过追问,荷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,并向小实道歉,保证不再犯错。小实表面上原谅了她,但心中对她的感觉已发生变化,渐渐产生了隔阂。最终,小实决然告别:“我的父母已经知道我们的事,他们不同意我和你结婚,否则将断绝父子关系。”荷花心知肚明,小实已经对她失望,尽管他说的是理由和借口,但实际上,他已经不再愿意接纳她。
两人痛苦分手后,荷花再也没有了当初的光彩,逐渐走向了堕落的深渊。她的神情恍惚、失魂落魄,常常神经质般的发呆,眼泪不止。她开始被客人避而远之,甚至成了“扛刀姑娘”,失去了曾经的光彩和吸引力。
因毒瘾愈发严重,荷花没有足够的钱购买毒品,她再次向金大发求助。金大发不再理会她,决定将荷花送到由英国人经营的戒毒院。在戒毒院里,荷花因为过度的精神压力,用头撞墙导致脑出血,最终死于院中。
最后,小实悼念这段不堪的过去,购买了荷花的棺木,将她送回杨柳青安葬。小实虽无力改变荷花的命运,但从他为荷花的最后安排来看,仍可见他是个重情重义的人。可惜,荷花的命运注定了她无法和这个好男人走到一起。她的早逝,或许反而成了她解脱的一种方式,早死早托生,或许对她而言是一种解脱。
这篇文章参考了《益世报》对“荷花之死”的报道,图片来源于网络,仅作示意,并非与文中人物相关。
发布于:天津市股票配资中心网站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